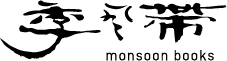筆者認為,近期中國政府釋法、港府修法,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官方對於主權的要求愈來愈嚴格。(資料照,AP)
文:莊嘉穎(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)
詳見: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3480876?mode=whole
為了《建國與國際政治——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(1893-1952)》(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: China, Indonesia, and Thailand, 1893–1952)的中譯版,我重新翻閱了多年前寫的文稿、筆記和收集的資料。當時研究的背景是美國進軍、占領阿富汗和伊拉克,不但推翻政權,還試圖重建政體和社會。這段殘酷的歷史,當時讓我對「主權」和「主權國」的源由起了疑問。畢竟,今天熟悉的「主權國」產生於17世紀,早期現代歐洲的政治氛圍,其法理依據出自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之際,參戰國簽署的《明斯特和約》(Treaty of Münster)和《奧斯納布呂克條約》(Treaty of Osnabrück)。2份文件奠定了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》(Peace of Westphalia)和現代「威斯特伐利亞式主權」的基礎。
這種強調高度集權、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的現代政治組織模式,雖然早在19世紀,就開始啟發許多不同民族和政治自決想像,但卻要等到20世紀中葉後,才開始真正在世界各地落實。其中,有1件事情讓我十分好奇:包括中國在內,有如此多民族、國族主義運動,經常宣稱自己不但代表某種正義,背後還有強大的民意,那他們確立主權國家的歷程,又為什麼如此漫長和艱難?其他包括殖民地和帝國的政體和政治組織,面對民族、國族動員時,又怎麼能維持數十年, 甚至上百年?後來發現,現代主權的建立和持續,其實摻雜了相當的偶然性。對脆弱政體而言,是否會形成主權國,經常取決於大國角逐下,所產生的衝突、抗衡、合作、干預,與「民族」、「國族」和「國家」意識的碰撞。中國今天的國家形態、台灣和香港面對的處境等,算是這些動態的一種案例。
國族主權國家的想像
在某個程度上,中國官方和民間堅持的領土主權,代表著一種權力和政治想像的結合。曾位於今天中國的各王朝、帝國,統治「天下」和主宰屬地的方式相當多元。從東周列國到大清帝國,不同統治者所持有的江山版圖,自古以來不斷演化。國家組織政治的形態,也一直改變。一度富有高度地方自治的漢代郡國制、清代蒙古族的盟部旗制、南宋稱臣向金國求和、琉球王國同時向薩摩藩稱臣和自認清國藩屬,這一系列作法與現代國族主權國(national state)制有明顯的差異。把國體的政治正當性和民族自我認知寄託在國族主權國家的想像,逐漸排除以往可能的彈性,縮減了領土完整問題上讓步的餘地。今天許多領土糾紛,是因為透過以往並不存在的主權、民族和國族主義視角,刻意詮釋疆土和海域,企圖使用國家機器和武裝力量,實踐全權管制而產生。有趣的是,讓香港能夠成功、繁榮,甚至帶動中國金融投資發展的特殊地位,就建立在國族主權國家的灰色地帶。
香港開埠於清帝國的割讓和租借地,在19至20世紀的戰亂和政治動盪中,給中國市場和外商提供相對穩定的自由港,成為促使多方可以獲益的關鍵經濟樞紐。這個位置確立在香港一方面與中國關係往來密切,另一方面又在英國管轄下,享有一套穩定、足以牽制行政權力和私人利益的制度,讓外界有信心投入。《中英聯合聲明》、《基本法》和「一國兩制」,當時就是希望在1997年後,能維持這種模糊的優勢。近期中國政府釋法、港府修法,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官方,認為實力上升,對於主權的要求愈來愈嚴格,不再容忍這種對主權的模糊尺度。台灣今天的自主空間,也可以說是立於不同國家形態之間的縫隙。今天的台灣在政治體制形式上,與其他主權國家並無兩樣,就差廣大國際的承認和國際組織的正式參與。這樣的處境反映中國官方和民間,長期把台灣視為國族主權中國所有,盡力否決台灣的國際空間,卻無法完全掌握台灣內政、外交。這種局勢其實也符合台灣的歷史脈絡。台灣本島上的原住民,直到日本殖民時期,向來不受外地政權管治。台灣在不同時段也經歷過殖民、被搬遷的政權當作根據地以及民主共和體制,政治定位不斷改變。連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曾各別宣稱支持台灣獨立。美國官方如今仍視台灣主權為「未定」(undetermined),頂多「認識到(acknowledge)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,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,而對此「不提出異議」。

筆者指出,香港位於國族主權國家的灰色地帶,成功發展出能夠帶動中國金融投資的特殊地位。(資料照,AP)
外力與政治組織形態
光靠想像,是不足以實質地影響如國家形態等政治組織。這類的變化背後往往需要一定的經濟財力和軍事實力。國軍和共軍在戰場上的表現再好,也沒有擊敗同時在太平洋和東南亞與美軍、英軍作戰的日本皇軍。最後是美軍投原子彈、蘇軍進攻滿洲,才迫使日本投降。在脆弱政體內部鬥爭的個別勢力,經常還得透過各種外力干預,才能立足,甚至得到最後的勝利。國共雙方能抵抗來自日本的強大壓力,部分是因為有來自美國和蘇聯的援助。毛澤東也幾度稱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獲得最後勝利,與日本因為侵華、打擊國民黨勢力有關。在抗戰時期的淪陷區,之所以沒有更大規模的起義,表示民眾或多或少接受日本統治。這可能出自畏懼,也可能出自生存或投機的考量,不過這種壓抑民族主權訴求的屈服,或許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經歷略同。
香港的歷史也充分表現了外力角逐和干預,對於政體形態的實際影響。香港的經濟樞紐角色,畢竟是經過英帝國積極爭取,其他強權因為可從中獲益而支持,以及清廷和之後歷任繼承政府的接受才能形成。即便日本1930年末代占領華南地區,東京還是一度容忍香港成為國民政府進口物資的口岸,直到1941年底日本帝國向英國開戰,占領香港。1950年代初,時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,稱與北京建交是為了「行個方便」(secure a convenience),從中以讓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繼續經過香港賺取外匯的方式,換取英國在香港地位的保障,使香港持續作為重要商業據點。若任何一方放棄或反悔,則會嚴重影響香港的繁榮、法治、開放、自由。今天中外經濟走向脫節,加上多方互不接受彼此對港政策,或許是香港模式面臨的最大挑戰。外力當然也對台灣政治形態有著極大的影響。國共內戰末期,除了國軍在古寧頭大捷戰勝之外,美國杜魯門政府因為不希望韓戰擴散,命令美國海軍巡邏台海,阻止國共雙方重新開戰,共軍主力又被調往朝鮮半島,撤退到台灣的國民政府才能在島上立足。後來1970代美中和解, 造成台北與華府中斷正式外交關係、脫離聯合國,但也促使台灣解嚴、民主化。美國對台灣的準安全保障和政治支持,和北京政府一時專注於經濟發展,暫時減緩了政治和武裝壓力,讓台灣雖然沒有正常外交,卻能鞏固內政和參與國際經貿往來。今天支撐著台灣高度集權、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,但缺乏國際承認的狀態,不但是島內民間動量,還有中美政治張力。若台美中之間,沒有一方徹底改變立場,那當前的局勢就不易更變。

筆者認為,台灣高度集權、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,但缺乏國際承認的狀態,不僅是島內民間動量、更是中美政治張力支撐而成。(資料照,AP)
外力長而持久的影子
外力對於政治組織和國家形態的影響,不限於歷史產物,它一直在不同地方發生和演變。中國推廣的「一帶一路」雖然表明沒有參與投資受惠國國內政治的野心,但是大量資金流入、基礎建設的建立,往往會影響當地在資源收益、成本和風險上的分配,因而可能改變在地政治和社會氛圍,甚至中央和地方的權威關係。從緬甸、泰國、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等地的經驗可見,自「一帶一路」貸款及其條件、給予中資的優先考量等情形,可能有意無意影響投資受惠國的施政,鞏固當地政權或引起政治湍流。在某個程度上,基礎建設發展和其他投資對當地情勢的影響,有些類似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,外力在中國各地貸款築鐵路、建立港口的現象。外來利益和資金湧入,無論來源、對象或動機,難免會對當地政治、社會和經濟帶來一定的衝擊。

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是習近平時代的核心外交政策。(資料照,AP)
一個政體無論是邊界劃定、政治組織形式,甚至國際參與,經常離不開外部勢力的角力、介入和拉攏。但是外力的影響並不一致。它當然可以造成分裂,有時也會促使體制變化,甚至可能推動不同國家形態的出現。如庚子事變之際,外力在加入八國聯軍等侵略性行動的同時,也因為自己的利益,力挺穩住本土政局和現狀的東南互保。主權國家想像的實踐,不是單靠內部情勢和民族或國族動員,往往還必須在適當的時機結合外力。類似現象不但曾在中國出現過,在東亞和世界許多地區也可以觀察到,特別是在本身勢力較弱的地方。
國族主權國大一統之類的論述, 之所以成為一種主流甚至正統,時常是其本土主張者在達到某程度的成效後,希望進一步鞏固或推動自己的立場,而作出的認知處理。這種形勢或多或少遮掩了外力在整個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。對以往經過的遺忘,或變相理解,甚至有助於新興壯大的主權國家,在有意無意中,複製以往外力對它的行為。在成功和壯大之後,原本處於弱勢、受外力深入影響的國家,都可能以經濟、政治、法律等途徑,介入其第三地。無論歷史背景,任何有足夠能力的行為者,在機會成本允許的情況下,也是可以對境外政體作出治外法權、最惠國待遇、以借款和發展方式掌握在地優勢、或是武裝干預等要求和舉動。許多帝國和殖民者,在建立自己勢力之際,也經常會以自己獨特、獨有的「道德」或「文明」,來解釋和美化自己的所作所為。或許沒有政治行者,包括脫殖或革命後的國族主權國家,能壟斷介入的行為、逃過介入的誘惑。

《建國與國際政治》書封。(季風帶文化)
*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,本文摘錄自:《建國與國際政治: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(1893-1952)》(莊嘉穎著、鄺健銘譯,由台灣季風帶出版)